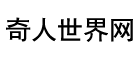北宋初年,东湖有个雅量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村上住有一位聪明过人的青年,名叫章添。他从小熟读诸子百家、医书典籍,博学多闻,就是年轻气盛、淡泊功名,只喜医道一项,因而到二十岁上,尚未娶妻。
这天他从深山采药回来,已是星夜时分,路过姑娘李翠家门口,听到室内有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不由暗吃一惊。他思忖:李翠父母双亡,家中就她一人,哪来这等声响?难道会背着人干那不知羞耻的勾当么!想到这里,心里好像吞下了一只苍蝇。
说来也是难怪,小翠父母双亡以来,犹似一只孤雁,唯有章添对她问寒问暖,爱护倍加,一颗心已暗暗系在她的身上。现在亲耳听到了这等声响,心里会好受么?谁知章添刚刚要走开,室内突然响起了打斗之声,章添来不及细想踹进门去一看,昏暗的油灯光下,李翠和一个半裸的汉子在床上滚作一团,李翠周身已被撕扯得一丝不挂,嘴角白沫四溢,似已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
章添目睹李翠受辱惨状,一股热血直涌脑门,大喝一声冲将过去。那汉子这时已从床上爬起, 两人一照面,章添不由自主刹住了脚步,天哪!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竟是县令的花花公子花春。
花春眼看到手的天鹅不翼而飞,恨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只见他双脚在床沿上一跺,一个饿虎扑食凌空扑向章添,双手宛似两把铁钳狠狠掐住章添咽喉。章添眼冒金星,几乎背过气去。
“章添!”趴在床上的李翠吓得惊叫出声。
被掐得昏天黑地的章添猛地听得李翠呼喊,浑身顿时来了精神。他一咬牙,将全身幸存之力聚于右臂,随着“啪!”的一声脆响,他那把紧紧捏在手中的药锄,已不偏不倚劈向花春的后脑勺,顿时,花春的脑袋像熟透的西瓜遇上菜刀“豁!”地裂开, 铁钳似的双手也似抽去了骨头,变得软绵绵,沉甸甸的身子成了一滩稀泥,歪向一边,转眼间,红的白的流淌了一地。
惊慌失措的李翠奔到章添身旁,见章添身子并无大碍,才想到自己还赤裸着身子,羞得双手掩面,赶紧返回身,穿衣不及。
章添见花春脑浆进流,再不动弹,料定必死无疑,就一步一捱向门口走去。
李翠见章添不声不响地要走,急得边系纽扣边呼唤:“到哪去?”
这时的章添倒是镇静,他慢慢回转身子,对李翠说:“花春既然已被我杀死,理当前去投案,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岂可连累了你!”
听了章添话语,李翠抽泣着说:“今晚要不是你,我定然遭贼子奸污无疑,哪里还有颜面活在世上?你救了我,反说什么连累,岂不是活活折杀我么?”说罢, 泪如雨下。
过了一会儿,李翠硬是止住哭泣,说:“添哥,你若前去投案,分明是羊落虎口,枉送性命,还不如趁月黑风高远避他乡。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日后自有出头之日。”
章添见李翠说得情真意切,心里亦是感动万分,便点头依允。临分手时,李翠拔下头上银簪, 递与章添,哀哀地说:“这银簪是母亲留给我的心爱之物,你带着作个纪念。日后如有会面之日,自然最好,若是无缘再见,你看见银簪,就似看见小妹一般。”
章添接过那带着李翠体温的银簪,藏入怀中,洒泪而别。依依不舍送走章添,李翠却不急着报案,直等到次日凌晨,估计章添已经远走高飞,官府再也逮他不得,方哭着去告诉地保。
地保匆匆赶到现场,一眼瞥见躺在血泊中的是县令的花花公子,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顾不得夜静更深,颤兢兢带了李翠前往县衙报案。
天刚放亮,地保和李翠已来到县衙堂前。耷拉着脑袋的地保有心想等县令起床用膳后再行禀告, 但又恐摊上个故意怠慢之罪, 因为死者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地保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像狗转坟头似的在衙前转个不停,后来见天空越来越亮,终于壮起胆子,击鼓不绝。
这时,躺在被窝里的县令正在做着黄粱美梦, 忽然被一阵鼓声惊醒,心里好不懊恼。
“哼!你们一对男女,大清早前来击鼓告状,是谁活得不耐烦了?”
小翠悲愤交加,突然昂起头,一字一句对县令说:“大人,此命案实在非同小可,请你暂时退去左右, 小的有隐情相告。”
县令见李翠生得眉清目秀,面上却似凝有一层寒霜,嘴角又噙着冷笑,嗑睡虫顿时逃走了大半; 又听她话语,似乎事关重要,倒也不敢小觑,略一沉吟,便挥手命众人退下,偌大一个公堂,眨眼间只剩下县令、 地保和李翠三人。
李翠见时机已到,便将河埠洗衣,遇见恶少主仆调戏,急急返家,又被跟踪;入夜,恶少闯门入室强行非礼,适逢村人章添路过相救,误伤恶少后脑至死的经过禀告得一清二楚,求大人为民申冤。
县令听罢,拍案怒道:“朗朗乾坤,竟有这等禽兽作反,实是死有余辜,但不知这恶少姓甚名谁,家住何处,说清了我自然会差人查清事实真相,依法论处。”
小翠见县令装腔作势,又说主仆素不相识,单记得仆人特征,颏下有一撮黑毛。
县令听得小翠说起仆人特征,惊得倏地从椅上悬起身子,追问:“可是长条脸,瘦高个子?”
李翠回答:“是。”
这下县令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竟如木头一般。半晌,才命手下将李翠、地保收押看守,自己则回到后堂,让夫人唤一撮毛前来。
自从李翠在堂上讲起仆人特征, 县令心里当即浮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撮毛、长条脸、瘦高个,除了夫人的娘家内侄,还会是谁?
县令知道,一撮毛跟随自己儿子多年,两人形影不离,如此事当真,那自己儿子肯定已去了阎罗大王那里了。
正自沉吟间,一撮毛被人唤到 ,县令铁青着脸问起儿子行踪。一撮毛见状不敢隐瞒,便将前因一一告知,果然同李翠所说一般无二,只是多了句:“夜里,公子不愿与我同往,我便先回来了。”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花春本是酒色之徒,平素寻花问柳,作孽不计其数,做老子的岂有不知之理。皆因自己也不是堂堂正正之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故而知道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当回事,这下遭了报应,做老子的却是痛彻心肺。他来不及责罚一撮毛,让人备上三匹快马,喊来一名心腹捕头,同自己一起跟随一撮毛驰往雅量村。
县令一行三人纵马扬鞭,临近雅量村,就望见村口有簇簇人影,等到村口,众人看清是官府来人,一哄而散。
李翠家一栋茅屋,竖在村口,周遭竹林菜地,并无近邻,一撮毛颤悠悠启开房门,一股血腥气刺鼻而来。血泊中,县令的公子恶少蜷缩着,整个身躯仿佛像一只硕大的醉虾。县令宛似五雷轰顶,霎时昏倒在地。
一撮毛和捕头小心翼翼护着县令回到县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堂吩咐衙役将李翠掌嘴三十,以戒其“妖言惑众”。可怜李翠打得口吐鲜血,脸庞肿得像发足了酵的馒头一般。
打完李翠,县令又编了个“造反嫌奸”的罪名,呈报州里,画影图形,悬重赏捉拿杀人凶手章添。
却说章添那夜急急逃离村落,一路马不停蹄,餐风露宿,进入喀山村寨,才驻足停下。
喀山是瑶民聚居的地方,民风淳朴,章添化名吕采,一来掩饰庐山真面,二来也是纪念李翠之意。
他在喀山就地取材,用中草药和针灸为当地群众治病,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和大家搅得很熟,瑶民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日子平平安安地过去,弹指间夏去秋来。与喀山紧邻的傍山寨, 有个妇女,怀胎十月,到了分娩之期,可小孩就是下不来。产妇已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全家大小哭成一团,在这死路一条之际,正好喀山有个村民出来探视,得知此事,便劝他们到喀山请吕采前来试试。产妇一家,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情,赴往喀山,请吕采救治。吕采正在煮饭,一听产妇命危,快马加鞭,随来人而去。
赶到产妇家,吕采也不歇气,径直走到产妇床前,一番望、闻、向、切后摇头说: “这难产确实非同一般,即使丸丹用箱装,药粉用斗量,也无济于事。”
众人听说,个个面如死灰,苦苦求吕采救命。
吕采恳切地说:“办法我有一个,只是时光实在拖得太久, 我也不敢说一定保险。”言毕,吕采让人舀来热水,取软布浸于其中,取出绞布,在产妇腹部轻轻揉摩,冷了再浸入热水,如此反复多次,待产妇皮肤泛红后 ,又让人移至产妇腰部,如法炮制。自己则用手在产妇腹部依穴按摩,一下,二下、三下……
突然,产妇身子一颤,“嘤嘤”几声呻吟, 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呱”地一声来到世上。众人欣喜若狂,把吕采当成了华佗再世。产妇全家趴在地上,磕头好比捣蒜一般。
待吕采将家人扶起,众人仍惊奇地问他使的是什么法术?吕采解释说:“这哪里是法术,我只是诊断,这些天来,婴儿虽然还在娘肚之内,但已离了胞衣,可能是一只小手捏住了母亲的脏腑,没有松手,故而,药吃得再多也似滚汤泼雪,难治根本。刚才,我在按摩时,已隔着肚皮,摸到了婴儿的小手,在他的手背上飞快地扎了一针,婴儿吃不住痛 ,手一缩就放开了,婴儿胎位原本正常,所以自自然然生了出来。”
吕采平平淡淡一番话语,说得大家将信将疑,于是就有人将婴儿抱过,仔细察看,嘿,天哪?婴儿白玉也似的小手背上还真有一处依稀可辨的小针孔呢!这下,在场人众没有一个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吕采整好药囊,打算离去,产妇全家哪里肯依,藏起药囊,杀鸡宰鹅,非得好好款待表表心意不可,左邻右舍也一应邀请作陪。
酒至半酣,左邻中一位专跑卖买的生意人敬酒说:“久仰先生大名,今日目睹,果然神技不凡。前时,我去汉地,偶得一纸,上面写满药名,想必是张方子,但又同普通方子不同,不知是何秘传,万望赐教一二。”说着起坐离席去取。
不过片刻,生意人已回转而来。吕采接过一看,那字迹却是轻灵飘逸,仔细一读,不由笑出声来, 只见上面写着:“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 谁使君子寄生缠绕它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述不尽黄连苦! 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 奈何!奈何!”
大家目不转睛瞪着吕采,盼他抖出谜底。
吕采停住笑,对众人拱拱手,解释道:“这上面虽有十二味中药名,却非药方,而是书信,倾吐了一位女子纯真的思夫之情,据传这位女子的丈夫也是才子,接到信后也回过一封嵌入药名的信,在下还依稀记得。”
至此,吕采朗朗背诵起来:“红娘子一别, 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苑。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姑待从客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日卷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与马勃、杜仲结伴还乡,至时有金银相赠也。”背完,吕采又作了说明。
这时,大家方知世上有此奇闻,抄写之人兴许也是个情种。谈着吃着笑着讲着,大家对吕采越益敬重起来,都认为他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奇人。光阴真像逝去的流水,一晃已到了一年一度的“三月三”。
“三月三”,是瑶家推选 “法头”的日子。“法头”,就是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官。
族规如此,吕采却是丝毫不知。这天,他为采摘医治邪毒的草药,天未亮就入深山,攀悬崖、 登峭壁、步深渊,直待采到草药,返回喀山,见家家门户洞开,却不见一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等走到中心广场,才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场中央,一堆篝火,烧得红艳艳、烈腾腾。他正想动问,出了什么事, 几个眼尖的青年男女早由地上跃起,几个虎跳,纵到他身边,欢呼着将他举上头顶。顿时,全场喊声、掌声响成一片。等吕采双脚踮地,身子已落在篝火前的平台上。
两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一左一右簇拥着他,在虎皮交椅上坐定,随着一声长啸,全场瑶民“刹”地一下俯身于地,天地间鸦雀无声。原来瑶民们经过选举,决定他为瑶家“法头”。这下他才恍然明白,不过木已成舟,他只好抱拳称谢。
“法头”既定,接下去就是告状时间。“咚咚咚!”三通鼓罢,一个瘦骨伶仃的汉子走上台来,朝他一低头,呜呜哇哇嚷个不停。
吕采见他双手比划、满脸泪水,竟是哑巴告状,听了半天,人似雾里看花,不明所以。正当情急之时,一个小童用木盘盛着茶点,送到了他的面前。吕采灵机一动,心里马上有了主意。
吕采拍拍哑巴肩膀,摇摇手,示意他别急;随后让小童转去取一块木板和一幅图画来,当着哑巴的面,指指木板,点点图画,叫哑巴把要讲的话用图画的形式表示在木板上。哑巴倒是挺灵,马上点头,捧着木板下台而去。
第二天,哑巴捧着木板图,兴冲冲来到吕采住所。吕采接过一看,心里不由得又是一征:只见木板上烫着许多焦黄的痕迹,图像行草凌乱,似乎被哑巴用烙铁烙出:木板左边有一个大凹坑,右边也有一个凹坑,排列对称,只是右边的凹坑特别圆;木板正中,是一支羽箭,但无箭头;木板边沿,锤有许多小洞,每个洞里穿着一根稻草绳。吕采将穿有稻草绳的小洞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二十个。望着这幅以锤代笔,以铁烫墨的奇画。
吕采百思不得其解,但瞥见哑巴那满是渴望的神色,心里又鼓起非破此案不可的勇气,于是微微一笑,指指哑巴的心,又指指自己的心,表示已经明白哑巴的心事,让他先回去,等候消息,自己则上“头人”和协同治理村案的“武卒”家里请教,可惜折腾了半天,依旧一无所获。
连续的挫折不但没能吓退吕采,反而更助长了他的斗志。回家后,他经过苦苦思索,决定走村串寨,一边替人防病一边访老问少,从众多的群众口中去寻找这诉状的谜底。
一天,他来到苗水寨给偏瘫老人吴伯治病,偏瘫是慢性病,不是一二日就能奏效的,他干脆宿在吴伯家,照顾、治疗吴伯。第七天的后半夜,他被一阵急骤的蹄声惊醒,急忙披衣起床,从窗孔中朝外探望,朦胧夜色中,三名蒙面汉子裹扶着十来头牛奔跑而过,“噼啪”的鞭梢声,不时响起。这时,吴伯也已醒转,他听到室外的响动,叹息说:“唉,作孽呀,真是作孽!”
他一听吴伯叹息,忙接口问道:“老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吴伯经过几日来的相处,知道吕采的为人,于是也不隐瞒,把其中缘由说给吕采听。
原来瑶乡北落有一个村寨叫龙目寨,寨中有个叫依穆的汉子好逸恶劳,专喜干偷盗牛羊的勾当,只是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专门邀集同伙到远地作案,因而近邻无人告发,远地又不知何人所为,使其恶行每每得逞。吴伯见识得多了,因而这次他不用起床窥看,凭直觉就可知道又是依穆一伙作案回归。
吕采听说,心里顿时灵光涌动,第二天一早,他暂时告别吴伯,回到喀山,邀齐头人、武座和瑶乡一应人众,在场中公开审判哑巴一案。
簪火熊熊,啸声阵阵,全场霎时一片死静。端坐平台正中的吕采脸若严霜,威风凛凛。半响,他才徐徐抬手,指向苍天,传令:“龙目寨依穆在哪?”两侧武士闻声,当即将依穆抓上台去。
依穆突然被抓,火从心起,破口大骂吕采有眼无珠,凭空冤枉好人,要头人和武卒主持公道。吕采不予理睬,只让哑巴捧着木板上台。
依穆一见哑巴上台,脸色顿时大变,但当看到哑巴手中的木板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符号时,神态又陡地蛮横起来。吕采并不与他计较,只将木板对着众人,将符号详细解释明白,等到讲清,依穆早 “扑通!”瘫倒在地。
连日查访,吕采虽说掌握了不少依穆的劣迹,但仍然解不开哑巴“诉状”之谜。 后来经过吴伯家的所见所闻,心里才猛然醒悟,再通过同头人,武卒的反复推敲 ,基本弄清: 木板图上从北往南的羽箭表示坏人从北方入侵两个对称的大凹坑。如果一个代表告状人哑巴 ,那另一个较圆的就代表“法头” ,因为在一般瑶民的心里,天和地是圆的,是最公正的,主持公道的法头自然也用圆形来表示。从劫持的牛群,吕采又联想到瑶乡拴牛鼻用的都是稻草绳,那么,木板图上穿有稻草绳的二十个小洞必定是有二十头牛被抢劫。照此推断图上毛毛草草焦黄凌乱痕迹则象征一群张牙舞爪的爪子在恶棍的指使下行凶作恶,至于羽箭不见箭头,则可理解为歹徒射箭伤人,箭头入肉,使人难以看见。
哑巴案真相大白,依穆供认不讳。吕采照瑶乡传统律例,判依穆赔偿哑巴的一切损失 ,并赤身裸体绳索缚身坐阴牢八八六十四天,
一伙帮凶都受到严厉惩处。接二连三的成功使吕采声誉大振,名气越来越大,不仅传遍了瑶乡每个角落,也外传到了州官闵文的耳中。
州官闵文为人正直,这段日子来,正为逮不到杀人凶手章添而耿耿于怀,忽然听到瑶乡冒出个汉人吕采,精通医道,断事如神,心里好生疑惑: 碰得巧的话,兴许就是章添也说不定!心念一起,闵文便命心腹捕头前去瑶乡探听明白,心腹捕头当即扮作货郎模样,摇着拨浪鼓前往瑶乡。
闵文等啊等,眼看半月有余,仍是音讯杳无,心里不免焦躁。这天,刚吃罢早点,却见捕头风尘仆仆前来复命。闵文本想责他息慢之罪,但得知“吕采就是画影图形悬赏捉拿的章添”时,满肚怒火顿时一笔勾销。
“章添啊章添,任你乖如鬼,也逃不过今岁!”欣喜之极的州官闵文当时就要调派兵丁前去捉拿。捕头见状连说不妥。为何?因为该州紧邻瑶乡,捕头和瑶民没有多少交道,素知瑶民“舍得一身剐,敢把天王老子拉下马”的剽悍秉性,因此,老谋深算的捕头以为:时下,化名吕采的章添声望如日中天,瑶民对他奉若神明,若盲目前去捉拿,惹恼了瑶民,说不定是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闵文见捕头说得有理,便问他有何良策。捕头倒不愧是混公门饭的,见州官动问 ,便把自己早已拟好的“百里奔袭,智擒章添”的妙计细细诉说一遍,并言明,这次去瑶乡之所以费了好多时日,是因为除了探明吕采就是章添外,还弄清了章添生活的规律,住地的环境和往来的道路,并说只要给我一名弟兄,四匹快马, 章添便能手到擒来。
闵文知道捕头颇有心计,就点头应允。
捕头从弟兄中选定一名壮汉,再加四匹良驹,择定月黑风高之夜,直扑章添住地。
夜色阴暗,但捕头对沿途道路早已熟记于胸,未到半夜,即来到章添所住村口。
捕头俩在村口僻静处稍事休息,取出干粮填饱肚皮,小心翼翼整理好马笼头和缰绳,才悄然进村。
两人摸到章添住屋门前,捕头一打手势,同伙就哼哼唧唧呻吟着,举手叩门。劳累了一天的章添,在迷糊中听见有人叩门,又听见病人哼哼, 只当有人急病求医,慌忙起床,打开房门。
门刚启开,闪身进屋的捕头就一招三式,左手倏地拧转章添手臂,右膝猛撞章添膝弯,右手一点, 大拇指和中指宛如两根鹰爪掐向章添颈项天鼎要穴,不要说章添不会武功,即使是会几下子,突然遭此闪电式的袭击,也难招架,章添只觉一阵钻心剧痛,几乎背过气去。此时,捕头的同伙已将一团破布塞入章添口中,再三下五除二同捕头将章添捆绑停当,抬上马背。捕头再翻身入室,照原样关好门户,然后腾身穿窗而出离开村子。
天刚放亮,捕头俩已快马加鞭逮着章添来到州衙,向闵文报捷。闵文闻报,喜不自胜,一面命厨下打点酒菜,亲自为捕头俩接风洗尘;一面命人将凶犯章添打入死牢,只待复核后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斩首示众。
三杯下肚,缓过气来的捕头将百里奔袭捉拿章添的经过一五一十禀告给闵文。
这厢庆功宴吃得喜气洋洋,喝得其乐融融;那厢却惊坏了闵文的女儿闵翠。当时,闵翠人虽在内堂梳妆,可两只耳朵却是一点也没闲着,当她听到章添被抓打入死牢等待向斩的消息后,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下倒在地上。
在一边服侍小姐梳妆的丫环见小姐突然倒地,且神志昏迷,顿时慌了手脚,连声大喊。闵文一惊,慌忙扔下酒杯,从椅上跳将起来。待他奔进内室,夫人和丫环已围着闵翠,掐人中的掐人中,揉胸口的揉胸口,折腾得团团转,幸喜不多一会儿,闵翠就悠悠醒转。
这时,闵文让人取来党参三钱,半夏三钱,当归一两,白芍一两,熟地一两,白术一两,川芎五钱,山萸肉五钱,天麻三钱,陈皮一钱,水煎服下。眼见闵翠的面色由惨白转向微红,闵文夫妇才松了一口气。
闵翠见父母为了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心里好生过意不去,因而也不等父母动问,便欠起身子,哀哀哭告说:“这章添实是女儿表哥,分别虽然多年,可女儿仍然记得,表哥生性忠厚, 绝不会做杀害无辜之事,还望父亲看在女儿份上,救他一命!”
这真是拳头里面生出巴掌,闵文乍听此言,几乎回不过神来,说: “女儿此话当真?”
闵翠又哭着说: “女儿怎敢在父母面前撒谎?若有谎言,任凭父母责罚。”
闵文沉吟半晌说:“自古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章添这厮杀人害命,造反嫌奸,远遁他乡,今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抓回,岂可纵虎归山!而父身为朝廷命官,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又怎可以己事私情,干徇私枉法之事?”
闵翠听父亲说得有理,便起身离床,两膝跪地哭告说:“若章添果然如父所说,则咎由自取,女儿亦救他不得,只恐内有隐情,冤枉了他,平白无辜做个屈死鬼!”
闵文面露不悦之色,义正词严地说:“女儿,你把老父当作何人?定案前,自要复审,杀人罪名属实,现当偿命,若有冤屈,我自秉公论断。”
夫人也在一旁相劝,闵翠这才含泪谢过。
次日清晨,闵文开堂审理章添案情,章添不喊冤枉,只是将上山采药,夜归时路过孤女李翠家,听得打斗之声,推门而入,见恶少正欲强奸孤女李翠,自已见义相救,反被恶少扑身,危急中才挥锄自卫,不料误伤人命的经过照实禀告。并说:“大人如若不信,可去当地传李翠一问就知。”
闵文见章添温文尔雅,不像凶残油滑之人。话语又说得恳切,便吩咐退堂,只待差人前往当地传讯李翠对证。
再说闵翠自闵文升堂以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坐立不安,好容易盼到父亲退堂,赶紧问询。
闵文说:“我已看在你的份上,一点也没用刑,结局如何,得看事实方可定性。”
闵翠谢过父亲,又恳求说:“女儿与表哥阔别多年,心里着实记挂,也不知道姨父姨母近况如何,父亲能否行个方便,让女儿同表哥见上一面,以慰渴望?”
闵文略一沉吟就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为父就依了你吧!”当天夜里。闵文暗中差人将章添悄悄带到后堂,教闵翠出来相见。
章添一见闵翠满身珠光宝气,长相却与李翠一样,惊得目瞪口呆。直待闵翠唤出“添哥!”这才如梦初醒,流下泪来。常言道,为人真到伤心处,英雄也是泪满襟!这一来,闵翠更是放声大哭。那哭声哀哀切切,伤心伤肝,任凭谁人听见,也难免下泪。
闵文觉得此情实非一般,便正色说:“你俩且止住啼哭,我看你俩不像表兄妹,真情如何,快快说个明白,下官自有道理。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
章添至此仍然不明内情,哪敢贸然开口,还是闵翠,见馒头吃到豆沙边,再瞒无益,只得跪在父亲面前,将前情如实禀告,那口词竟与章添堂上所述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临分手时将头上银簪相赠”一句。闵文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闵翠竟是李翠。
原来李翠自县衙回家后,乡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打量她,自己觉得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再想到自己原本同章添两情相悦,这次又赤身露体在他的面前,此身自然非他莫属,于是就起了外出寻找的念头。她找出亡父穿过的旧衣,女扮男装,奔波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日出日落,潮聚潮散,李翠随身带的盘缠早已用尽了,身子憔悴得形同乞丐,不但没能获得章添半点生死存亡的讯息,有几次还险些被人瞧出庐山真面目,弄得胆颤心惊。
一天,绝望的李翠来到燕子崖,望着头顶茫茫苍天,脚下滔滔江水,悲叹天地虽大,却恨无章添、李翠栖息之所,毅然跳崖舍身殉情。
也是李翠命不该绝。正当她纵身跳下崖头坠入江中,上游就有一艘官船如飞赶来,船上官员见有人投江自尽,急急吩附水手快快抢救。
说起这船上官员,正是闵文,闵文带着家眷是赴州上任。这天,天高云淡,闵文出舱,踱上船头,凭栏跳望燕子崖风光水色,亲眼目睹了李翠投江的镜头,李翠才侥幸得救。
李翠被救上船,闵文让下人替她更衣施救,方知是女儿身。
待李翠悠悠醒转,已在官船后舱。闵文同夫人细问所以,李翠不知内幕,哪敢实说,只说自已名唤翠翠,哭哭啼啼编造出一段“父母双亡、外出投亲不遇,难以为生”的经历搪塞。闵文夫妇俩见她身世可怜,先动了恻隐之心;又见她虽是穷途落魄女子,但生得身材窈窕、举止温柔,仪容不亚大家闺秀,心里更增添了三分喜欢;再想到自己并无子嗣,便有意认她作个干女儿。李翠凭空得此好运,哪会不愿,就五体投地行了跪拜大礼,闵文夫妇给她定名为闵翠,随船赴任。
李翠、章添泪水涟涟,闵文夫妇俩听了也唏嘘不止。章添从怀中摸出李翠相赠银簪,恭恭敬敬奉与闵文验看。闵文慨叹说:“汝且收好,我自有理会,只是案未了结,还是委屈您一下。以免走漏风声。”章添应声,随差人去死囚牢监押。
这里闵文命捕快火速前去传唤当时陪同李翠上县投案的地保;另遣人去当地暗中查访花春劣迹;再密嘱心腹捕头去县衙四周伺候,一见面上长有一撮毛的家伙,当即拿下,只是需要做的秘密。
不久,地保传唤到堂,证实李翠所述前情均系事实,探查花春为人的差役也收得花春平素许多狗仗人势的恶行。闵文一一记录在案。
再过几天,一撮毛被捕头用麻袋兜头套住,神不知鬼不觉,抓捕归案。
万事俱备,闵文宣布升堂。一撮毛跪在地上,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好像抽去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大老爷饶命!”
闵文只这一句,就把心怀鬼胎的 一撮毛吓得屁滚尿流,哆嗦着将自己同主子花春的罪行交代无遗,然后磕头犹如捣蒜。
冤情大白,闵文行文上司,控告县令纵子行凶,残虐百姓,制造冤狱诸多罪责,要求将他革职查办,并当堂宣告章添无罪。退堂后,闵文将章添唤至内堂, 命仆妇端上好茶,和颜悦色地问章添道:“此番你冤案已了,不知今后作何打算?”
章添见老爷问得恳切,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小人为此案牵累 ,远走他乡已是数载,也不知父母如何生活,今蒙大人明察,冤情得以昭雪。自当早归故里,悬壶行医,侍奉双亲颐养天年。”
闵文点头道:“难得你一片孝心!不过,近日来,我已知你和翠儿情意非常,按理说,我也该成全你们才是,可……”
说到这里,岗文皱着眉头打量着章添,沉吟不语章添见说到自己和李翠之事,一颗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低着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闵文摸着颏下胡须缓缓说道:“翠儿自从跟了我们夫妇之后,已是一个端庄俊俏的大家闺秀,我们视她为掌上明珠。 前些日子,知府刘大人派人来说亲,刘公子一表人才,同翠儿自是门当户对,你为人虽好,但毕竟……”此时, 闵文一声长叹,再无下文。
章添听了,起先暗暗叫苦。后转念一想,又觉得,李翠自从被闵文夫妇收为义女后,自然每日里锦衣玉食,仆妇环侍,远非昔日荆衣布钗面容憔悴的村姑可比,纵然她真情如初,但我若娶了她,岂不苦了她一生?罢罢罢!想到这里,章添不由把心一横,贴身取出银簪,奉与闵文道:“大人,李翠现在是府上千金, 小人怎么不知天高地厚?请你将此簪归还于她,就说我祝她幸福吧!”说毕拜了两拜,起身告辞而去。
却说李翠知道章添已无罪释放,正在内堂与义父叙话,就满腔喜悦地入闺房梳妆打扮。梳洗未毕,义父渡进房来,手中捏着一根银簪,竟是自己送与章添之物,心中巨震,忙问义父: “章添何在?”
闵文摩着翠儿黑发,怜爱地说道:“翠儿啊,爹娘待你可好?”
李翠感激答道:“爹娘侍翠儿胜过亲生父母, 再好不过了!”
闵文点头道:“实话说,我们夫妇从来就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盼你嫁个好人家,日后也好有个依靠。日前,知府刘大人托人给儿子求亲。想那刘公子学识过人, 与你正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为父便答应了他,此事为父已说与章添知道,章添倒也有自知之明 ,要我将银簪归还于您,从此楚河汉界两不相干。”
李翠听了,恍如巨雷击顶,几乎背过气去,泪水竟似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落个不绝。闵文见李翠不言不语,心中亦觉没趣,便安慰了几句,强调做爹娘的是为她好,才怏怏离去。
从此以后,李翠只字不提婚事,对闵文夫妇却是更加孝顺体贴, 端茶送饭,问好请安,乐得闵文夫妇笑逐颜开,只是常见李翠房中灯光深夜不灭,闵文夫妇俩心里有些担忧,后来见李翠起居如常,并未有失态之处,也就慢慢放下心来。
时光如逝水,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清晨,丫环慌慌张张来报:“老爷、夫人,不好了,小姐不见了!”
闵文夫妇闻报大吃一惊, 急忙赶至李翠闺房,但见人去楼空, 桌上端端正正放着两套折叠齐整的衣衫和一封书信。闵文匆匆拆开,见信中写道:
小女禀告:不孝女多灾多难,年仅四岁,慈父早逝;行年十四,母又下世,孤苦一人,赖添哥一家照顾。年前,小女身遭飞来横祸,全仗添哥舍命相救,前时, 小女在燕子崖自尽,意亦为添哥殉情,先承父母相救,又蒙父母哀怜收为义女,养尊处优,恩重如山。小女自思报恩犹为不及,又岂敢擅自违抗父母之命焉!只因女儿身遭横祸之时,曾亲口许身添哥且以银簪为凭,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现岂能以父母为官显达因富贵而食前言?小女无添哥,无以有今日;添哥无小女,无以乐天年;望父母怜悯小女愚诚,同情小女私衷,小女则生当陨首死当结草,不敢为忘也!谨百拜叩首。
闵文看罢,顿足长叹,夫妇俩捧起衣衫,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